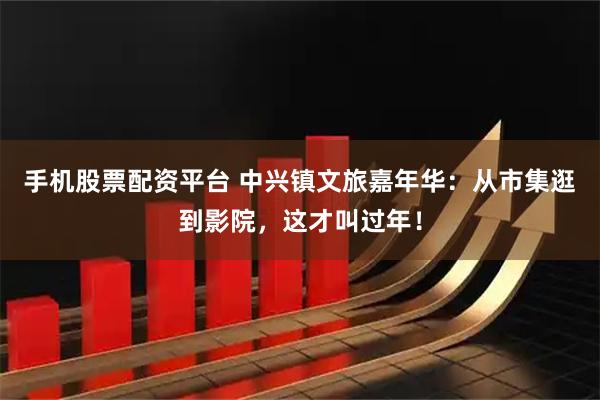1991年盛夏专业配资开户,檀香山的空气带着海盐味。长达半个世纪的软禁结束后,已迈入九旬的坐在落地窗前,望着太平洋的波纹发呆。记者递上录音笔,想听他回忆一生最难以释怀的节点。张学良只是摆了摆手,低声一句:“西安事变,我不悔。”又停了几秒,他补上一句:“但杨宇霆那一枪,错了。”短短两句话,把外界多年猜测拉回到1920—1930年代那个刀光剑影的东北。
要理解张学良“错杀”的心结,得先回到1928年冬天。当时的奉天城昼夜飘雪,甫遭日本关东军炸死,军政大局顷刻失衡。张学良虽是公认的嫡系继承者,但在奉系军阀内部,他并非举足轻重的唯一人选。——这个出身普通、性格强势、精通兵工制造的陆军少将,被许多老奉军视作“更能镇场面”的人物。东北军里管他叫“杨督办”,连日本情报部门也把他排在“最应重点拉拢名单”前列,可见其分量。
1930年前后,张学良忙着修整军纪、整合关外财政,杨宇霆则手握兵工厂、后勤、参谋权,等同掌了东北军的腰杆子。两人表面兄长相称,底下暗潮汹涌。杨宇霆更习惯用“我为东北谋划”那套说辞,说服部下直接向他汇报。奉天督办公署的账本到了张学良案头,经常发现凭空少出大笔军饷,流向却无从追查。这些细节,像不断加码的筹码,把张学良推向决断的边缘。

时间很快跑到1928年末。南京国民政府电令东北易帜,蒋介石希望借此完成名义上的国家统一。张学良的判断是:顺应大势,暂避日本锋芒,再谋后局。杨宇霆却认为,此举无异自缚手脚,他甚至在幕僚会上直言:“东北凭什么听南京调遣?”一句话点燃双方冲突的火药桶。
有意思的是,就在易帜争执最激烈的那周,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悄悄加派人手,“关东军司令部”三个字频繁出现在杨宇霆的私人日程笔记里。张学良得到情报,心里发寒——若任由杨宇霆抗拒易帜,关东军趁乱介入,满洲恐怕瞬间沦为殖民试验场。
1929年1月7日这场“寿宴”成为导火索。杨府灯火彻夜未熄,蒋介石、白崇禧、阎锡山的代表乃至日本政要皆送礼祝寿。宴桌上,有宾客当着张学良的面说“杨督办才是东北人心所向”,场面一度尴尬。回到帅府,于凤至忍不住低声嘀咕:“他杨宇霆俨然东北主人。”这句话敲在张学良脑门,杀机开始成形。
三天后,张学良以讨论铁路督办公署为名,请杨宇霆与其心腹常荫槐到督军府“喝茶”。那间老虎厅宽敞却阴冷,墙上挂着张作霖游猎时的相片。临行前,副官悄悄塞给张学良一块铜币。相传,他抛了三次:“正面杀,反面放。”三次皆正。又反设条件再抛三次,仍然同样结果。试想一下,他本不信命,这一刻却像抓到某种宿命提示。
1月10日下午两点,老虎厅枪声短促。杨宇霆和常荫槐当场倒地,事件被定义为“军纪整肃”。与此同时,张学良命令厚葬两人,以示“私人情义未绝”。从此,他再无东北内部掣肘,易帜顺利完成,国民政府对东北的名义统合尘埃落定。不得不说,从政局稳定角度看,这抉择是有效的;然而张学良个人却背负了难以消散的负罪感。
六年后,1936年12月12日,爆发。张学良以军事行动逼蒋介石“同意抗日”,震动国内外。事件虽令他遭到长久软禁,却削弱了内战,将主要矛头转向对日战争,在学界普遍被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转折。因而他坚称“不悔”。可奇怪的是,追念往昔,他每每谈到1936,大多神情轻松;反而提及1929年那声枪响,眉梢总会浮现一种难言的犹豫。
1991年那天,记者追问缘由。张学良沉默良久,忽然开口:“如果那时我能再等一等,也许还有别的办法。”这是史料中难得的自我检省。晚年的他攻读圣经,迷上绘画,似乎用另一种方式赎罪——一幅幅水彩,总在角落画一缕若隐若现的白雾,看似随意,旁人却猜那是东北的寒潮,也是杨宇霆的亡魂。
历史研究者不必做道德裁判,但可从多重角度评估这段往事。其一,日本对东北的觊觎注定会放大奉系内斗,没有强硬的权力整合,易帜难成;其二,张学良个人权力巩固的速度,直接影响关外抗日资源调配;其三,军事将领的互疑、自负、派系利益交织,很容易把正常的政治分歧升级成血腥清洗。这三点放在一起,就能理解为什么张学良说“最悔”却又迟迟走不出阴影——军事理性与人伦情感的撕裂,常常在一念之间。

也许再过许多年,关于东北失守、关于张、杨二人的是非,仍会有学者提出新的档案与新解读。庄严的史料之外,这桩往事仍昭示一个朴素结论: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,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会合流,任何权力手术都付出高昂代价。至于张学良晚年那句“错了”,无论用何种角度剖析,已化作无法挽回的历史印痕。
2
嘉创资本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